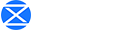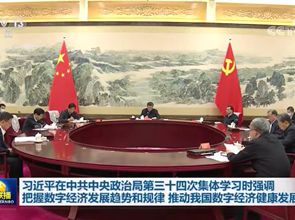目前我國(guó)數字經濟和實體(tǐ)經濟融合仍主要依托消費互聯網,數字化轉型在供給側、産(chǎn)業鏈中(zhōng)的滲透仍存在不平衡、不充分(fēn)、不深入等問題,亟須健全數字生态系統,進一步釋放數字經濟新(xīn)動能(néng)。
近年來,我國(guó)數字經濟蓬勃發展,新(xīn)技(jì )術、新(xīn)業态、新(xīn)模式加速滲透到經濟社會各領域。《中(zhōng)華人民(mín)共和國(guó)國(guó)民(mín)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(yuǎn)景目标綱要》指出,充分(fēn)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(yòng)場景優勢,促進數字技(jì )術與實體(tǐ)經濟深度融合,賦能(néng)傳統産(chǎn)業轉型升級,催生新(xīn)産(chǎn)業新(xīn)業态新(xīn)模式,壯大經濟發展新(xīn)引擎。
數字經濟與實體(tǐ)經濟的深度融合,是黨中(zhōng)央立足全局、面向未來做出的重大戰略抉擇,是我國(guó)“十四五”及中(zhōng)長(cháng)期經濟實現高質(zhì)量發展的必然選擇。但也必須看到,目前我國(guó)數字經濟和實體(tǐ)經濟融合仍主要依托消費互聯網,數字化轉型在供給側、産(chǎn)業鏈中(zhōng)的滲透仍存在不平衡、不充分(fēn)、不深入等問題,亟須健全數字生态系統,以大數據中(zhōng)心、産(chǎn)業互聯網平台等數字化基礎設施為(wèi)抓手,實現生産(chǎn)服務(wù)、商(shāng)業模式、金融服務(wù)等各利益相關方的數據融通,促進對數字技(jì )術的利用(yòng)和數字化服務(wù)的訪問,進一步釋放數字經濟新(xīn)動能(néng)。
實體(tǐ)經濟轉型的着力點
産(chǎn)業鏈的聯動關系決定了實體(tǐ)經濟數字化轉型需要從生态的角度出發尋求着力點。
首先,數字生态可(kě)重構主體(tǐ)關聯模式,發揮網絡效應。實體(tǐ)經濟要實現數字化轉型,不是單個企業的“孤立”行為(wèi),而需要政府、企業、服務(wù)商(shāng)等多(duō)方協作(zuò)。數字生态為(wèi)轉型相關主體(tǐ)之間的協同發展提供了新(xīn)空間。通過構建數字生态系統,龍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經驗得以固化、推廣、複制;中(zhōng)介服務(wù)商(shāng)通過識别共性需求并提供模塊化解決方案,為(wèi)企業和産(chǎn)業突破數字化轉型技(jì )術壁壘,降低轉型成本;政府以數字生态為(wèi)依托提供更多(duō)、更完整的具(jù)有(yǒu)公(gōng)共物(wù)品屬性的數字基礎設施,服務(wù)實體(tǐ)經濟數字化轉型。
其次,數字生态可(kě)重構産(chǎn)業鏈關系,優化資源配置。傳統鏈條式的産(chǎn)業鏈、供應鏈關系,在數字生态中(zhōng)由于各主體(tǐ)的關聯模式重構而随之發生改變,形成網絡結構下的短鏈模式,以高效的業務(wù)協同、數據協同、要素協同,實現價值共創、利益共享。對于産(chǎn)業鏈上遊,數字生态助力企業實現智能(néng)化供給,保證産(chǎn)業鏈供給安(ān)全;對于同類型企業,借助數字生态下知識共享、技(jì )術共享、産(chǎn)能(néng)共享、訂單共享、員工(gōng)共享等多(duō)種數字化模式創新(xīn),實現優化資源配置,提升競争優勢;對于産(chǎn)業鏈下遊,數字生态打破生産(chǎn)與消費相互割裂的狀态,将生産(chǎn)、商(shāng)業、消費、社交有(yǒu)機融合,借助數據分(fēn)析優化産(chǎn)品設計、産(chǎn)能(néng)投放,精(jīng)準匹配用(yòng)戶需求,提高有(yǒu)效供給。
再次,數字生态可(kě)對接全球市場,助力支撐雙循環。當前國(guó)内外經濟形式複雜多(duō)變,黨中(zhōng)央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(guó)内大循環為(wèi)主體(tǐ)、國(guó)内國(guó)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(xīn)發展格局。數字生态為(wèi)企業特别是中(zhōng)小(xiǎo)企業拓展全球化市場建立新(xīn)通道,提供了信息展示、貿易洽談、支付結算、稅收通關等各環節的全面數字化服務(wù),大幅降低交易成本,提高交易效率。通過基于數字平台的供需對接,為(wèi)企業精(jīng)準定位海外需求、融入全球産(chǎn)業鏈、供應鏈提供新(xīn)途徑,是新(xīn)時代背景下實現雙循環的有(yǒu)力支撐。以“絲路電(diàn)商(shāng)”為(wèi)例, 2019年我國(guó)與22個夥伴國(guó)家的跨境電(diàn)商(shāng)進出口額達245.7億元。
數字生态發展有(yǒu)“三難”
數字生态是數字化發展中(zhōng)各參與方共建共治共享的利益共同體(tǐ)。但目前我國(guó)基于産(chǎn)業互聯網平台的數字生态建設仍處于初級階段,存在發展、融入、評價等多(duō)方面挑戰。
一是數字生态發展難。目前存在平台型和鏈式兩種類型的産(chǎn)業生态圈。前者由互聯網企業主導,具(jù)有(yǒu)跨界産(chǎn)業屬性,主要提供資源匹配和技(jì )術服務(wù);後者由垂直領域大型企業主導,主要深度鏈接産(chǎn)業鏈的上下遊企業和用(yòng)戶,涉及能(néng)源、交通、制造等基礎國(guó)民(mín)經濟領域。
這兩類生态圈分(fēn)别在産(chǎn)業縱向和橫向聯接方面發揮着重要作(zuò)用(yòng),兩類生态圈融合發展是大方向,但目前仍存在困境。從内循環視角看,平台型生态圈的發展需要來自中(zhōng)小(xiǎo)企業和用(yòng)戶的信任和支持,要鼓勵它們積極融入數字生态;鏈式生态圈通常都是圍繞大型企業原有(yǒu)的供應鏈和用(yòng)戶,容易陷入封閉型生态圈。從外循環視角看,一方面受中(zhōng)美貿易摩擦和科(kē)技(jì )競争的影響,數字生态外向發展容易受到國(guó)外政府限制;另一方面,數據隐私保護體(tǐ)系、數據跨境流動準則,甚至是技(jì )術價值觀和技(jì )術倫理(lǐ)等已成為(wèi)我們數字産(chǎn)業“走出去”的重要阻礙,容易成為(wèi)歐美政府限制我國(guó)數字生态發展的靶子。而解決這些問題,需要政府和市場共同發揮作(zuò)用(yòng)。
二是數字生态融入難。廣大中(zhōng)小(xiǎo)企業對融入數字生态既渴望又(yòu)擔憂,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:首先,企業資金投入不足,傳統中(zhōng)小(xiǎo)微企業,難以承受數字化轉型的成本,各地數字化轉型扶持政策一般優選互聯網企業,傳統中(zhōng)小(xiǎo)企業享受不多(duō);其次,企業對轉型認識不足,大多(duō)中(zhōng)小(xiǎo)企業僅僅關注平台的流量帶動能(néng)力,因而目前零售、娛樂類等靠近消費端的企業對數字化轉型較為(wèi)積極。許多(duō)制造業企業運用(yòng)數字技(jì )術的能(néng)力不足,對設備或業務(wù)系統上雲到底能(néng)解決什麽問題不清楚,上雲意願低;再次,企業上雲信心不足,企業決策者擔心數據上雲後被雲服務(wù)提供商(shāng)“偷窺”利用(yòng)或遭到洩露;最後,企業政策激勵不足,從目前各地出台的數字化轉型政策措施看,多(duō)集中(zhōng)于從企業外部提供硬件和軟件的技(jì )術支持,而對企業數字化轉型戰略、人才等内在要素的培育力度不夠,尚未能(néng)從根本上激發中(zhōng)小(xiǎo)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内在動力。
三是數字生态評價難。開展數字生态發展評價将有(yǒu)助于引導企業積極擁抱數字化、融入數字生态;輔助政府以數字生态為(wèi)主體(tǐ)把握數字化轉型的進程,發現問題,制定政策。但目前對于如何評價數字生态在融合中(zhōng)發揮的貢獻仍不清晰,存在“評價難”問題。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:首先,企業融入數字生态帶來的效率改善、效益提升全面滲透于實體(tǐ)經濟生産(chǎn)過程和産(chǎn)品,且與企業其他(tā)要素的投入具(jù)有(yǒu)協同效應,很(hěn)難将之從企業産(chǎn)出中(zhōng)剝離出來;其次,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利益相關方的競争關系由傳統完全競争的排他(tā)性關系轉變為(wèi)利益共享的共生性關系,正确評估數字生态中(zhōng)的競争和競争動态是數字生态評價中(zhōng)的核心,将有(yǒu)助于政府制定和實施相關監管和反壟斷政策、措施;最後,數字生态評價體(tǐ)系尚未形成統一認識,對數字生态的價值評價比單一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評價更加複雜,不僅僅是投入産(chǎn)出關系,更需要從生态帶來的創新(xīn)力、消費者福利、平台治理(lǐ)創新(xīn)、可(kě)持續發展、創造創新(xīn)等維度加以綜合衡量。
亟待制度與技(jì )術協調推進
“十四五”期間,發展面向供給側的數字生态是激發數字經濟新(xīn)動能(néng)的重要抓手。為(wèi)保障數字生态長(cháng)效發展與有(yǒu)效賦能(néng),需形成以政府為(wèi)主導、市場積極參與的協作(zuò)模式,共同推進數字生态治理(lǐ)制度和技(jì )術應用(yòng)創新(xīn)。
第一,打造互信、包容、開放的數字生态環境。一是落實國(guó)内促進數字生态良性發展的法規制度。加快落實《個人信息保護法》,并進一步明确數據共享與确權規則,加強數據保護,明晰平台、企業與用(yòng)戶之間的權責利關系。二是鼓勵發展互利共赢的數字生态,推廣“利益相關者至上”的平台經濟思路,并加強平台監管,消除大衆對平台壟斷的擔憂。三是在規範基礎上進一步向市場有(yǒu)序開放醫(yī)療、交通、教育等領域的準入資質(zhì),促進民(mín)生領域數字化深入轉型。四是建立并發展國(guó)際數字生态建設聯盟,搶占國(guó)際數字規則制定先機。加強國(guó)際協商(shāng),建立與歐美、東盟以及“一帶一路”沿線(xiàn)國(guó)家的數字經濟貿易、跨境數據流動等規則,積極參與全球數字治理(lǐ)。
第二,提升數字生态的賦能(néng)和創新(xīn)能(néng)力。一是推廣平台數字化賦能(néng),加強政策引導和落地,地方政府積極推進本地企業與數字平台的對接,宣傳推廣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投入産(chǎn)出效果,完善新(xīn)型公(gōng)共基礎設施建設,實施财稅政策引導企業借助平台上雲用(yòng)數。二是發揮平台創新(xīn)作(zuò)用(yòng),借助平台創新(xīn)商(shāng)業模式能(néng)力,創新(xīn)場景應用(yòng),以場景應用(yòng)帶動産(chǎn)業融合發展。三是提升數字生态的技(jì )術創新(xīn)叠代能(néng)力,建立基于平台生态實現技(jì )術創新(xīn)的機制,發展關鍵核心技(jì )術。發展開放式平台合作(zuò),協調政産(chǎn)學(xué)研關系,政府加強資源協調和整合,科(kē)研機構承接基礎技(jì )術研發,高校提供複合型創新(xīn)人才培養,企業實現技(jì )術産(chǎn)品化,平台實現成果轉移轉化匹配并輔助提升企業生産(chǎn)制造和産(chǎn)品推廣能(néng)力。
第三,完善數字生态價值貢獻評價體(tǐ)系。一是加強對數字經濟、數字生态測算和評估的理(lǐ)論體(tǐ)系和方法學(xué)研究,從機理(lǐ)上認清數字生态在數字經濟與實體(tǐ)經濟融合中(zhōng)的貢獻作(zuò)用(yòng)機制和特征。二是加快數字生态評價統計體(tǐ)系建設。建立國(guó)家統計部門與大型數字平台提供商(shāng)的數據連通與共享,開展數字生态發展相關指标的構建和統計調查,為(wèi)數字生态價值貢獻評價提出數據基礎,提高數字生态統計數據在數字生态價值評價中(zhōng)的使用(yòng)程度。三是建立多(duō)元化數字生态評價體(tǐ)系。辯證地看待數字經濟與實體(tǐ)經濟融合過程中(zhōng)的競争與創新(xīn)關系,從數字生态的基礎設施、服務(wù)供給、創新(xīn)能(néng)力、社會福利、可(kě)持續發展等多(duō)個維度全面構建數字平台的價值貢獻評價體(tǐ)系。
作(zuò)者單位:中(zhōng)國(guó)科(kē)學(xué)院科(kē)技(jì )戰略咨詢研究院
來源:科(kē)技(jì )日報